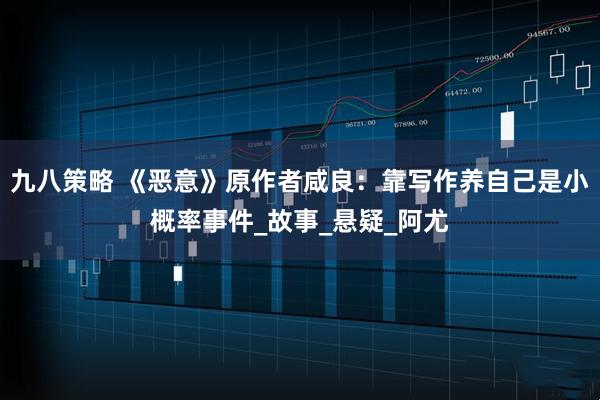
自己写的小说被搬到大荧幕上,是什么感受?
本期播客我们请来了电影《恶意》的原作《恶女阿尤》的作者咸良。
2019年,一次偶然的动笔,让咸良写下了这篇9万字的小说;
他也成了「ONE一个」举办的「故事大爆炸」征文大赛当年的长篇首奖获得者。
是热爱的驱使还是生活的所迫?
是表达的冲动还是机遇的巧合?
今天,我们和咸良一起聊了聊,关于全职写作、投稿获奖和影视改编之后。
扫描下图二维码即可收听本期播客完整版内容。
编辑部:什么契机让你决定要参加故事大爆炸的投稿?
咸良:当时个人处在一个比较混沌的时期,做生意,和朋友开店,赔了。然后自己也不知道要干什么,之前的一些事情也不赚钱了。在瓶颈期刚好就看到了比赛。自己之前还写过一两个中篇的小说,就想试一试,反正那个时候我的时间也不是很值钱。觉得试一试也无妨。
展开剩余90%编辑部:所以《恶女阿尤》这个故事是在征文期间写的,还是之前就写好的。
咸良:征文期间写的。我看离截止只有最后两个月了,就赶了一下,然后最终写到 9 万多一点,刚好就压线就投了。
编辑部:做生意钱打水漂了,当时会觉得投稿能赚钱吗?
咸良:100% 是打水漂的事情,我是带这样的心态,但当时状态并不是说是我要投稿了我就要赚钱,因为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,就想各个方面都试一试,至于钱这个事,想都不敢想。
编辑部:那你是从小就热爱写作,并一直保持写作习惯吗?
咸良:那倒不是,小时候就是写作文嘛,几乎没人喜欢写作文,小时候写东西更多的是和学习绑定在一起,没有形成自我的习惯,所以我对写作就还好,也不抗拒。
编辑部:《恶女阿尤》是你的第一部小说吗?
咸良:不是的,之前写的几部作品都是中篇,又很短,大概三四万字,《恶女阿尤》算是当时写的最长的一部了。前几部也有卖掉版权,也有在改编电影的,所以这给了当时的自己一点信心,想着是不是能够再继续写写,反正那时候闲着也是闲着,那就再坚持一下。
编辑部:《恶女阿尤》这个故事的灵感来源是什么?
咸良:你们还记不记得?大概在 2017、18年的时候,有一个新闻事件——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。我在小说里面也提到这个事了,就是以这个事件作为一个灵感来源。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事件是一个创作动力来源。当时看了这个事就觉得很愤怒,然后就想写点啥。
编辑部:当时看到是写医患题材觉得还挺大胆的,你当时是怎么想到切入这个故事角度的呢?
咸良:很多年前有一个案件,在医院里发生的一起罗生门事件,一个孕妇在医院里跳楼,有孕妇、有医生、有家属,三者之间不停掰扯,但最终真相是什么大家都不知道,最后孕妇跳楼了也闹得特别大,医院本就是社会冲突比较聚焦的一个地方,我觉得是很有探讨价值的。
图源:电影《恶意》
编辑部:悬疑故事是你最擅长的写作类型吗?
咸良:会擅长一些,但是悬疑可以是一种类型,也可以是一种风格,也可以是一个写作的技巧。
只不过对我来说,可能悬疑这个东西更容易让故事写得好看一些,因为我是理工科出身,逻辑还行,用悬疑可能更容易勾得住人,读者才会有更大可能性去体会你想表达的内容。
从内容和表达本身来讲,其实并不受悬疑这个题材所局限。比如说如果你的文字写得很漂亮,如果你的氛围描写得很好,那你能勾得住人就更好了。
但我在这些方面做不到,就只能用悬疑这个东西来勾一勾人,大概是这么一个感觉。
编辑部:眼下人工智能很火热,你觉得AI 写悬疑小说的话,它会有自己的优势吗?
咸良:我前段时间还确实研究过这个事,可能AI的信息组织能力比较强,但写出来东西到底怎么样?其实还是比较奇怪的,你稍微有一点阅读基础或写作基础的话,就会发现它还是没有那么的智能,可读性还是比较差的。而且它思考的逻辑链很诡异,它会假装思考,我觉得它和人脑还是不太一样,暂时还不太能替换掉我们写字的人。
编辑部:给「故事大爆炸」投稿之后大概多久得知自己获奖消息的?有想过自己会拿奖吗?
咸良:可能有一个多月,编辑通知我的作品入围了,入围后又过了一段时间,大概在过年前后,确认了自己拿奖的消息。
当时确实有点意外,作品刚写完那会可能有那么一瞬间会觉得,哇,我还挺厉害的,居然写完了,但要说拿奖是没太敢想的,毕竟有奖金的诱惑在,我自己是很期待的,不过稍微冷静下来就知道,这个获奖是个小概率事件,就跟买彩票一样。
编辑部:这个作品是非常适合进行改编的,这个议题在很多悬疑题材上是很少见的,大家普遍看的都是一些凶杀题材,重点都在杀人诡计上,但这个故事看完之就会发现,它在真相之外还有更深层的表达,特别是观影过程当中,好像隔着屏幕也变成了网络那头的一些观众一样。而且看这个故事的过程中,一度误以为你是学传播学的。
咸良:我是理工科,专业是学物流工程的,专业学科上更多的是给我提供了思维帮助,转到写作后,其实我还挺顺利的,发现自己确实对写作更感兴趣。
编辑部:那除了兴趣驱使外,你的个人经历会对创作有帮助吗?
咸良:早年我从事自媒体行业的经历吧。刚开始我也是跟你们一样做过播客,后面又做了文字自媒体,那时候赶上了算法主导信息分发的野蛮增长的时代,那段经历是密集接触互联网信息的阶段,而且因为有自媒体经历,就会从接收方和输入方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,也会不自觉关注这些社会议题,这些经历非常大地帮助了我对互联网传播方面的理解。虽然《恶女阿尤》写了两个月,但整个故事从出现、构思到完成,可能在前些年就有所积累,这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。
编辑部:你提到这个故事是受到社会新闻影响下才创作,我们在观影过程当中,也会想到之前一些热搜,那还有哪些现实中的事件是对创作有帮助的呢?
咸良:这里面我写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事件,小说里提到小孩脑瘫治疗的事,这是当时比较著名的一个有争议的新闻,到现在这些都在互联网上查得到,但因为热度一波一波过去,真正需要挖掘的东西,反而被一些噱头给淹没了,我是觉得比较遗憾的,所以在创作故事时会带入这种情绪,希望大家能更多的关注到后续。
编辑部:这个故事创作时最难处理的是哪个部分呢?
咸良:最困难的部分可能是如何真实平衡地处理一体两面的特性,比如不论是人、事件或者参与其中的媒介,一方面要保证情绪的浓度和冲突,又要利用冲突感把表面的东西划开,到达一个表达的最深处。打一个比方,比如说两个掰手腕的人,两个人的手里面拿着一把手术刀,如果稍微有一点不平衡就完蛋了,本来是做手术救命,结果变成了拿刀子杀人,这个感觉就会完全不一样,可能这部分是我觉得最难处理的。
编辑部:写故事时会把自己带入到某一个角色或是某一个视角吗?比如这个案子中的警察视角还是媒体主编的视角?
咸良:我多数可能是偏记者这边一点,但每个角色我都挺喜欢的,都会疯狂代入,代入了就可能会有不同的这个心态。小说里面有一个角色叫陈福军,不知道电影里面有没有改动,但在小说里面我觉得这个角色离我们普通人更近一点,他身上我称之为凡人之光的东西,是比较能让我共情的。
编辑部:在成长过程中有哪些作家/小说/电影对你产生了影响?
咸良:很难讲是哪本书或者是哪部电影有具体的影响,更多是整体性的,像吃饭一样,一口一口吃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我看电影会多一些。主要是被电影塑造的,哪怕是一些好电影、烂电影,但是看了很多电影之后,在电影里面一定会有一些共通的,你所认可的和你的感受相匹配的东西,然后最终提炼出来,成为了你个人价值观或者是人生观的一部分,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就是所谓电影文化的一种力量。
编辑部:刚刚说看电影的影响,如果看电影解说可不可以?
咸良:也可以啊。包括现在我们说到刷短视频的这个事,我们有一段时间经常会说是刷短视频不好,分散你的注意力,让你无法专注,你接受的碎片信息不好。但是我最近在想一个问题是:短视频真的不好吗?
有的时候我在想我们当年比如说读书、看电影的时候,电影、书这些可能更多也是别人的二手信息。但是我们刷短视频的时候反而能刷到一些更原生、更自然、更一手的信息,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以前忽略的部分,而对于搞创作的人来说,可能我们需要的一些素材养分更多是要来源于一手的东西。
编辑部:写作是一件需要耐心的事,在创作中有没有想放弃的时刻?
咸良:很多,特别多,可能也得分情况看,比如如果是一个故事的话,真的是时时刻刻想放弃。逼自己也没有用,写不出来就是写不出来,如果真的让我写得极度痛苦,那就放弃呗,没有什么,写不出来说明火候不到,这可能会对应另一个瞬间,就是某一个时刻你有压抑的表达欲,这个时候不写也痛苦。
编辑部:现在靠写作能赚到钱吗?会不会有生存压力?
咸良:靠写作养活自己这个事,坦率地说不是一个聪明的选择。
相比于当下的其他谋生手段,这不是一个有性价比的事情。我算是比较幸运的,我这几年确实是靠写作还能维持正常生活,就比如说是编剧、小说的一些费用就还可以,但是整体来说还是充满了不确定性,生存压力还是很大。
而且这种焦虑反过来会影响你的创作,会恶性循环。所以如果你不是那么坚定,那么热爱,或者说是你没有一个基础保障的话,不要辞职来写作。
编辑部:得知影视改编时,哪些情节和元素是希望导演保留和强化的?
咸良:我觉得都可以改,唯一期待就是舆论之善、人心之善的这部分不要牺牲掉了,我觉得这是这个故事真正的力量。
编辑部:希望观众在观影后对故事有怎样的新理解和新感受?
咸良:我也在期待,也想知道观众看完到底会有哪些反应。当时在one一个app上发布时,我看了很多读者的评论反馈,很多角度是我没想象到的,等电影出来之后,应该可能会引起更大范围的讨论,也一定还有更多、更有趣的东西。
编辑部:这几年我们也目睹过很多起网暴事件,你如何看待网暴或键盘侠这一群体?
咸良:仅从网络暴力本身来讲,网络暴力是一种结果,指责网络暴力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点政治正确的空话,更重要的是找到背后原因和症结所在,是媒体不作为,还是媒体失责,还是相关信息披露不透明?还是别有用心的谣言等,这些元素在影响舆论的发展,比跟风的键盘侠评论的权重要大。
不得不承认有一部分人的确是充满恶意,但大部分人可能是没有主观恶意,只是被舆论裹挟的,而这些注意力,需要被正确引导。
编辑部:《奇葩说》节目里有个辩题“键盘侠算不算侠”,你是怎么看的呢?
咸良:我觉得算。只要把舆论的注意力,舆论的刀,声量的刀,架在该架的地方,这就是侠。但如果架错了地方,就会出问题。
编辑部:整个故事是还原真相的过程,你觉得当前网络生态下,真相还重要吗?或者说还有被还原的空间吗?
咸良:重要的,即便在当下真相没那么容易出来的时代。我之前看过一篇文章,讲的是“公共说理空间的消失”,我觉得这个很准确,当下社会人们觉得真相难寻,大家也会对所谓反转和真相感到疲惫,即便如此,真相依旧有意义,哪怕大家没达成共识,但过程仍然是宝贵的,它会打破个人的盲区,我认为真理不怕被讨论。
编辑部:在观影过程中,对普通人有可能在网络放大镜之下被审视被评判感到毛骨悚然,你怎么看这种情况?
咸良:个人层面来讲,谨言慎行是很重要的,就是处于自我保护的状态。我觉得人们会越来越有这种意识了,这个是没办法,环境所迫嘛。
另一方面我觉得教育或法治还是需要一步步地跟上,现在确实是有一个滞后的情况。
编辑部:根据现在电影市场来看,悬疑题材是不是对影视改编的帮助更大,更有优势呢?
咸良:无论是电影还是小说,悬疑这个类目它准入门槛不是很高,也有天然吸引人的东西,毕竟有个钩子放在里面,人的好奇心在这里。看起来是有一些优势,但要想做出精品,门槛就比较高了。
编辑部:那今年的「故事大爆炸」你还会继续参与投稿吗?
咸良:我不知道能不能写得完,写出来了就投。
编辑部:你觉得能在「故事大爆炸」获奖的作品应该具有的特质是什么呢?
咸良:我个体的经验太没有参考性了,可能是得写出属于自己的特点?不论是主题、表达方式、文字风格等,至少在某个维度上要有亮点。
编辑部:能否给还在坚持写作,想投稿「故事大爆炸」的朋友提供一些可参考的建议?
咸良:我到现在来讲也是一个没有那么有经验的人嘛。不过我可以分享一个心得。
可能许多作者,尤其是新人作者比较在乎的一个点是:我作为一个新人,我投了会不会不被在乎?我觉得不会。
据我对「故事大爆炸」的理解和接触下来的感觉,它更看重内容本身,而不在乎你的身份或者你的资历,你的名气或者你的噱头。在当下这个很仰仗名头的时代,非常可贵。
所以对新人来讲,不要有顾虑。不管你是不是新人,只要内容好就有机会,认真写,放心投。
和咸良聊天,我感受到的是在今天,在很多对话中,少有的真诚。
他不避讳自己做生意赔钱的经历;
也不吝啬表达自己对当下网络现状的看法。
重要的是,在他身上,我看到了属于普通写作者的可能性。
一个动笔时刻的诞生,也许非常意外。
可能是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的迷茫阶段;
可能是一份无法自抑的表达冲动;
但就是这样一个契机,才让好故事被看见,甚至被搬上大荧幕。
这是属于普通人叙事的时代;
博牛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